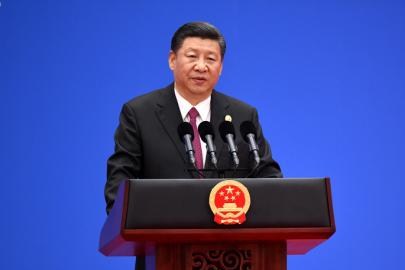有多少种方法可以让我们走进一个国家?
去旅行,或者去看别人的旅行风光照?去吃一顿异国风情的大餐?也许最经济实惠并且最能提供想象空间的办法,就是去阅读属于这个国家的文学。
今天,青阅读邀您一起去一趟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拥有1万多片海滩,即使你每天去一个全新的海滩,也得花费你27年多的时间。而我们可以通过文学更快速、更深度地抵达这里,文学可以告诉你这个国家所经历的过去,能告诉你百姓在当下的生活里关心着什么,亦能给你关于未来的答案。
日前,第十届“澳大利亚文学周”在中国举行,四位澳大利亚知名作家来到中国,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哈尔滨等地与读者见面讲述澳大利亚的故事。幸运的是,四位作家齐聚北京,分别接受了青阅读记者的专访。四位作家各有专长:历史写作、非虚构写作、儿童文学及绘本的创作。很难用一个具体的词来概括澳大利亚文学的特点,因为关于这块大陆的秘密,都在字里行间。
Australian
托马斯·肯尼利: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结尾太蠢了
现年82岁的托马斯·肯尼利是个和善的老头儿,在北京的这几天,他无时无刻不在与人聊天,从未觉得疲惫。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只有花白的胡子能透露他所经历过的岁月。圆圆的肚子里仿佛装满了故事,他可以随时给旁人讲出很多故事,他自己的故事,他听来的故事,他创作的故事——当然和他有关的故事中最为人知晓的,一定是被斯皮尔伯格改编成电影,并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辛德勒的名单》。是的,这部电影的小说原著《辛德勒方舟》(后更名为《辛德勒的名单》)就是他写的。
《辛德勒方舟》是托马斯·肯尼利偶遇到的一个故事。1980年,他结束了意大利电影节之旅回到澳大利亚,因为要在洛杉矶转机,他在洛杉矶闲逛了一阵,“我准备去买一个公文包,那家店的店主Leopold和我聊天,他知道我是一个作家之后,说必须讲一个故事给我。”这位店主告诉托马斯·肯尼利,他本人是辛德勒救下来的幸存者,“他和我说了很多,他的讲述很有力量。”那一刻,托马斯·肯尼利便产生一种将它写下来的冲动,“我看着他,我好奇为什么纳粹想要杀他们,我想不通他们为什么想要杀掉这些人,就因为他们感到这些人对欧洲文明产生了威胁吗?我觉得很难理解,所以我对这件事非常感兴趣。”
这个纳粹时期的故事对托马斯·肯尼利还有特别的意义,这让他想到自己的父亲。“之所以对希特勒的政权很感兴趣,是因为我爸爸是一个澳大利亚士兵。二战期间他去了北非,在那一地区反抗纳粹势力。他会给我寄回一些战利品和纪念品,这些从埃及带回来的德国的物件让我印象深刻,也让我对这个政权有兴趣。”托马斯·肯尼利告诉记者。
这本书的创作并不轻松,“最开始我甚至是拒绝的,我和Leopold说,我写不了这个,列出了我不是犹太人等等理由。但是后来我觉得也许可以做一些研究试一试。”他搜集了大量资料,然后对犹太文化萌生出很大兴趣,“为这本书我还去了波兰,当时波兰还处在戒严时期,商店里没有什么东西,人们说话的时候要窃窃私语,他们非常小心……”
谈到斯皮尔伯格对小说的改编,托马斯·肯尼利说,这是一部很棒的电影,电影的影响力确实远大于小说,让这个精彩的故事被更多人知道,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他并不喜欢结尾让人流泪的那一段,“结尾的时候,当辛德勒痛哭流涕地说我如果卖掉这辆奔驰车,就可以多救几个人……我觉得这个段落太蠢了,并不符合这个角色。他如果真的这么做,就是个笨蛋了。” 因为他和斯皮尔伯格对结尾的分歧,让这部小说的电影改编推迟了十多年,“Leopold在中间做了很多沟通,他时不时地给斯皮尔伯格打电话,说: 奥斯卡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故事,你得拍这个反映了伟大的人性的故事,你拍那些毛茸茸的小动物的故事得不了奥斯卡奖。 ”这部电影最终获得金像奖的时候,托马斯·肯尼利和Leopold都很激动,“Leopold一直在重复着说我早就说了这是个好故事,我早就跟你说了,我早就跟你说了……”
在《辛德勒的名单》以后,他没有停止写作,他的创作从宗教主题的《三呼圣灵》到美国传记《亚伯拉罕·林肯》都颇富历史厚度。托马斯·肯尼利告诉记者,他喜欢历史,但也会对战争写作有天然的兴趣。“我觉得这和我父亲曾经是一名士兵有关,作为作家,我相信战争更好地反映了人性。如果没有战争,作者们就只能写一些虚构的风流韵事。”他顿了一下,然后笑着说,“不过,爱情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啊。”
杰拉尔丁·布鲁克斯:
从记者到作家,我变得更自由
长大以后要做记者,是杰拉尔丁·布鲁克斯8岁时就决定的。在报社工作的父亲带杰拉尔丁·布鲁克斯到单位参观,报纸采编和印刷的流程让她非常震惊:“我意识到在报社工作可以比所有人都更早地了解到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我感觉太刺激了,当时我就想要做记者,后来大学所学的一切专业都指向这个职业发展。”大学毕业后,杰拉尔丁·布鲁克斯在澳大利亚做了三年记者,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硕士毕业之后她先后为《华尔街日报》和一些澳大利亚媒体供稿。
杰拉尔丁·布鲁克斯几乎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驻外记者,更没想过目的地是政局纷纭的中东和非洲。“那是我人生中最紧张最激烈的一段时间。” 她说,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报道是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以后,“库尔德人在北伊拉克地区建立了库尔德地区自治政府。那时,出于采访需要,我必须要非法进入北伊拉克地区进行报道。所以我们就从叙利亚出发,沿着底格里斯河,最终到达伊拉克的北部,那是一段让我很难忘记的旅行。”有机会接触到新闻现场,便可以得到第一手的资料,杰拉尔丁·布鲁克斯说,因为目击让她有机会独立思考,而不是被他人的声音左右,“我在中东做报道期间,我对很多问题感到好奇,譬如伊斯兰国家妇女的问题。我很喜欢报道伊朗,因为我认为这个国家被人们误解了,美国人对伊朗和伊朗人的印象并不客观,我认为伊朗的文化和社会非常不同寻常。”她希望用自己的笔,更深入地报道伊朗,“让美国读者看到一个真实的伊朗。”
她的非虚构写作是现实和历史并行的。新闻采访是日常的部分,不超过3000字的篇幅时常让她感觉并没有把一个问题说透,渐渐地她想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向纪实文学与历史书写的创作中,“对我来说,从记者向作家转变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写好一个故事,把情节发展下去,并且吸引读者。”
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有了新闻调查和文学写作这两种能力就具备了创作的基本技能。当然要完成一本书,还需要有面对历史的耐心。她的作品《奇迹之年》就是这样诞生的——这个小说以真实的历史故事为背景,讲述了1665年英国村庄经历的黑死病。在北京期间,杰拉尔丁·布鲁克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的讲座上与读者分享了这个故事创作的始末:起初她和先生一起在英格兰乡间登山,她的丈夫发现了这个村庄,在当地教堂他们看到了相关记载,“伦敦的鼠疫被传染到这里,当地村民做了不寻常的决定,他们没有选择逃亡,而是全部留下来。作为记者我很想知道当时人们如果做出这样的决定,又是如何在2000个邻居相继死去的时候活下来。我认为应该把它写下来。”这部小说花费了她三年的时间,功夫不负有心人,小说出版后大获成功。
也正是从这本基于历史的纪实小说之后,杰拉尔丁·布鲁克斯完成了自己记者和作家身份的转变,她创作的《马奇》获得2006年普利策奖。论及记者与作家的区别,杰拉尔丁·布鲁克斯认为,作家意味着更多自由,特别是她当了妈妈以后,“过去很多年,我的生活都被新闻占据,卡扎菲扔了个炸弹,我就必须要上飞机,所以当我有了孩子,继续新闻工作太难了,有些人很成功地平衡了母亲和记者两个身份,而对我来说,如果你不能百分之百投入就做不好一个好记者。所以改写小说变得容易很多,生活变得自由许多。”
这次来到中国,她见到了很多老朋友,很欣喜地看到北京有很多变化。谈到对中国的了解,杰拉尔丁·布鲁克斯说自己最近正在读《三体》。“这本书棒极了,作者充满想象力,同时又很擅长描述科学原理,他让物理变得如此鲜活。” 此次的中国之行,她也并未忘记自己做记者的老本行,“我希望自己可以了解更多年轻的中国作者,看看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
Writers Week
布朗温·班克罗夫特:
大自然是最好的艺术老师
布朗温·班克罗夫特刚一打开酒店的房门,一份特别的礼物就让她激动得跳起来——由她绘图的绘本《下大雨了》中文版放在她房间最明显的位置迎接她。“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太开心了。”她眉飞色舞地说,耳环上的极富民族特色的彩色羽毛飘来荡去。
布朗温·班克罗夫特出生于澳大利亚的一个土著村落,村子里只有不到3000人,从小她就和大自然亲密无间,“小时候我们常常去丛林里游泳、散步,那里人烟稀少,自然是你最好的朋友。”长大后她从事设计工作,用线条描绘属于澳大利亚的人文风情,笔触间满满都是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我从小就很喜欢画大自然,澳大利亚的自然环境太美了,它启发我的所有创作。”
地理环境是我们看到的世界的样子,同时它也会无声地形塑着我们表达的方式。对于大部分中国读者来说,每到夏天,暴雨往往也会给心头带来乌云;情况在澳大利亚会有不同,这本薄薄的绘本《下大雨了》讲述了澳大利亚沙漠地区的小朋友们大大的期待——年迈的史蒂夫叔叔和孩子们生活在沙漠,在旱季他们迫切期待一场降雨,孩子们不停地问爷爷,下雨了吗?下雨了吗?爷爷总是回答说,再等等,再等等……直到大雨倾盆而至,所有的孩子们都手舞足蹈地欢呼,非常开心地冲到雨中。
“过去30年,我创作了40多本儿童绘本,我喜欢选择一些日常生活中的故事,通过图画来和读者分享这些属于澳大利亚的故事。” 除了用画笔记录自然,布朗温·班克罗夫特会在绘画中倾注她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大自然是最美丽的事物,我也在用作品表达我对自然的态度——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护自然,要小心地、聪明地适应并且保护这颗星球,因为我们这代人会死去,我们还有后代要继续生活在这里,小朋友也要从小知道爱护地球的意义。”
创作绘本之余,布朗温·班克罗夫特还会参与到各种各样给孩子的艺术项目中,她到儿童教育机构给孩子们讲绘本,教小朋友画画,她的儿子也开创了一个专门为原住民开设的教育机构,“他让我录了很多视频,向孩子们展示如何画画。”一提到绘画,布朗温·班克罗夫特就会笑得很舒展,因为这是让她的灵魂自由生长的地方,“对我来说,绘画就像氧气一样。我让孩子们很自由地画,想画什么画什么,我的角色就是告诉家长,让孩子们弄脏自己的衣服吧!因为我们会花费整个一生来创造,所以在孩子们的幼年阶段保护他们的创造力很重要。我也会教一些大人画画,有的人可能50年没有碰过画笔了,他们上一次画画可能是六七岁时的事情,所以他们长大以后也没有从事任何创造性的工作,好可惜。”
艺术的天性需要从小启发,用色彩表达自己是一种方式,读绘本也是一种方法。在布朗温·班克罗夫特看来,绘本不仅是孩子的专属,还应该是成年人与孩子的艺术之桥。“我觉得所有成年人都应该给孩子读绘本,第一,你可以通过读绘本和你的孩子建立联系。第二,当你给孩子读儿童绘本的时候,你可以结合你的个人经历给孩子讲故事,分享一些看法和观点。在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会给孩子念我创作的绘本,有时候还会在故事的基础上讲点别的,这就好像是我和孩子的一段共同旅程。” 布朗温·班克罗夫特鼓励读者在读绘本的时候更多地去寻找图片里的秘密,“那些缤纷的图片中有很多细节,教孩子阅读和看图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但归根到底是一件快乐的事。”
in China
约翰·马斯登:
让孩子们拥有直面现实的力量
一个父亲会给自己的六个儿子讲什么晚安故事?一个青少年小说家会给全世界的小读者讲什么故事?这些问题约翰·马斯登给了我们答案。
花白的头发,熨帖的衬衫,微微鼓起来的肚腩,戴在无名指的戒指,翻毛皮鞋——这让约翰·马斯登看上去很稳重,与他最广为人知的“青春冒险系列小说” 《明日战争》里营造的战斗青年的形象完全不同。《明日战争》系列故事已在中国出版多年,中国青少年读者应该对这个故事并不陌生,约翰·马斯登讲述了7名高中生到一个偏远的小镇远足露营,回到家时发现澳大利亚已经遭受武装入侵,他们不得不拿起武器展开反击。这群年轻人直面战争,在胜利和失败的交错中增长了勇气,也完成了自我的成长。
尽管这个系列的故事漂洋过海,让约翰·马斯登的名字被全世界所知并让他获得“澳大利亚青少年畅销小说创作之王”的美称,但约翰·马斯登觉得自己早年写的这个系列故事并不算是很成熟,他并不是特别喜欢别人把“青少年冒险小说”的标签扣在他身上,“我认为那种打怪升级、把坏人抓起来的想法是很幼稚的,那些真正有力量的故事应该来自人们对精神力量的发现。”约翰·马斯登有六个儿子,给自己的孩子讲故事的时候,他会更多地告诉孩子们如何找到精神的力量。“我会给我的孩子们讲一些自己编的故事,但是也会从希腊和罗马寓言故事中找到一些灵感,我希望孩子们能够成为日常生活中的英雄。”
日常生活中的英雄和幻想小说中打怪战斗的超级英雄有什么不同呢?这要从约翰·马斯登写过的几本没有被翻译成中文的纯文学小说说起了。“这些作品中没有爆炸、没有灾难,小说的主人公都是普通人,他们不断应对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问题,竭尽全力寻求人生的意义,试着让自己的的生活变得更好,不断让自己的内心世界平和的同时,也可以帮助周围的人。对我来说,真正的英雄就是这些人。我喜欢探索这样的人的内心世界。” 约翰·马斯登告诉青阅读记者。
接受采访时,约翰·马斯登更像是一个严肃文学作家,他把文学看成一件庄严的事情,是一件离商业社会很远的事情。《明日战争》系列刚刚出版造成轰动时,曾有63家电影公司找到他,争相要买下电影版权。他拒绝了那些挥着钞票的制作方,“我看不惯电影公司觉得他们很有钱,好像什么都可以买下来的样子。”多年后,又有一个电影制作方找到他,“他没说能给我多少钱,而是说看中了我的故事,我才同意让他们拍摄这部电影。”电影在澳大利亚公映那天,约翰·马斯登到现场去了,当他看到自己的读者热泪盈眶的时候,自己也有点动容。
当然,这部轰动澳大利亚的青少年冒险小说也有批评的声音,故事中不乏战争的场面,虽然并不是宣扬暴力,但这也引发不少澳大利亚家长的担忧。约翰·马斯登觉得,让孩子们有面对现实的勇气并不是坏事。“日本导演黑泽明在12岁的时候目睹日本大地震,他哥哥带他去街上走,看到很多尸体,但当晚黑泽明却并没有失眠。第二天早上,黑泽明问哥哥,为什么看到了骇人的一幕却还能睡得很好。他的哥哥告诉他,那些你害怕直视的东西,才有能力伤害到你。所以,一旦你有能力直视那个东西,诚实地面对它,它就失去了伤害的能力。”约翰·马斯登说,当他创作那些关于战争作品时候也在这样想,“我竭尽全力地去展现关于战争的每一个角度,因为我相信,小说的力量就在于揭示真实的现实。”